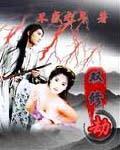道教之性命双修
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祖师主张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,认为宋儒主理,禅家主性,道教主命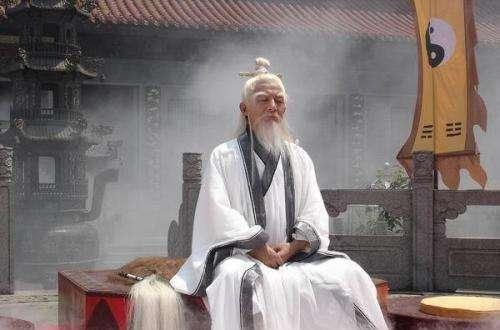 要求弟子们要以《道德经》为根本的情况下,借鉴《心经》和《孝经》的教意,在举止上,持守儒家的忠孝观念,弟子要忠君守法,孝敬父母,百善孝为先!识心见性,全性保真,“外积阴德以济世,内练真功而修真。”
要求弟子们要以《道德经》为根本的情况下,借鉴《心经》和《孝经》的教意,在举止上,持守儒家的忠孝观念,弟子要忠君守法,孝敬父母,百善孝为先!识心见性,全性保真,“外积阴德以济世,内练真功而修真。”
全真教龙门派的祖师丘处机把师父的理论发扬光大,提出了“性命双修”。“性”就是脱离人们肉体而存在的真性;“命”则是与人的肉体相关联的血气与脉络。在修性上,以炼心为主,提高素养,积功累德,以求得真性显现。在命功上,倡导内丹方术,强调调理气息,营为气血,炼气养神,追求练形保精。认为“见性为体,养命为用,三分命功,七分性学。”他的成仙界论为即要有精神上的逍遥自由,又要有肉体上的健康长久。
其实人生本应如此,用一颗好的心态,承载一副健康的身体,不去理会生理年龄的大小,用无所谓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。只要心态好了,身体健康了,内心喜悦了,未必要上天,每天都是神仙似的人生!
何为“道教的双修”?
道教养生家提出的性命双修的思想,是建筑在形神统一的生命观上。一般而论,性命和形神是两对可以相通的概念。性与神是相通的,均指人的心性、精神、意识等;命与形也一致,是指人的生命、形体。但由于时代的先后与观念的演变,称谓和内涵也就有了相当的差异。在汉唐时期的养生家,多称“形神共养”。唐宋以后的内丹家,则多称“性命双修”。从思想内涵上看,汉唐养生家的形神共养理论缺乏完整性,方法上比较零碎单调。而宋元内丹家的性命双修的理论,却非常完整,方法上也相当系统丰富,从而达到了十分精微的程度。
关于“性命”二字,儒释道三教各有不同的理解,道教内各个宗派亦有各自的看法。就道教内部而言,一般地讲,“性”指心性,理性,又谓之“真意”“真神”等;“命”指生命、形体,又谓之“元精”“元气”等。内炼心神为性功,外炼精气为命功。元代全真派大师丘处机指出:“金丹之秘,在于一性一命而已。性者天也,常潜于顶;命者地也,常潜于脐。顶者性根也,脐者命蒂也,一根一蒂,天地之元也,祖也。”故丹家千经万论,只此性命而是。
南宗初祖张伯端说:“道家(指他以前的传统道教)以命宗立教,故详言命而略言性;释氏以性宗立教,故详言性而略言命。”在他看来,性命本不相离,道释本无二致。“彼释迦生于西土,亦得金丹之道,性命兼修,是为最上乘法,故号曰金仙。傅大士诗云:‘六年雪岭为何因?只为调和气与神。一百刻中为一息,方知大道是全身。’钟离正阳亦云:‘达摩面壁九年,方超内院;世尊冥心六载,始出凡笼。’以此知释迦性命兼修。”
从《悟真篇》来看,这确属张伯端的主张。该篇七绝第一首即批评禅宗之徒说:“饶君了悟真如性,未免抛身却入身,何以更兼修大药,顿悟无漏作真人。”谓单修禅宗不如兼修内丹。至于佛教下乘禅法,更被斥为下乘。《悟真篇序》曰:“唯闭息一法,能忘饥绝虑,即与二乘坐禅颇同,若勤行而之,可以入定出神”,其最高功果也不过达到内丹派所谓五等仙中最下等的“鬼仙”。
张伯端自认己家之说为性命双修,故无所偏,最为圆满,乃得三教先圣性命真传的正宗。究其实际,则是直承魏伯阳《参同契》之说。内丹以人身精气神为三宝,精气属命,神属性。从《钟吕传道集》、《灵宝毕法》看,五代钟离权的丹法,从修命入手,循序渐进。至吕洞宾、陈抟,受佛教禅宗影响,倡性命双修。张伯端继承了这一思想,更加强调性命必须双修,以此融合三教。
白玉蟾再传弟子萧廷芝,发挥张伯端性命之学。他说:“夫道也,性与命而已。命者有生也,性者万物之始也。夫心者,像日也;肾者,像月也。日月合而成易,千变万化而未尝灭焉,然则肾即仙之道乎?寂然不动,盖刚健中正纯粹精者存,乃性之所寄也,为命之根矣。心即佛之道乎?感而遂通,盖喜怒哀乐爱恶欲者存,乃命之所寄也,为性之枢纽矣。吁!万物芸芸,各归其根,归根曰静,继曰复命,穷理尽性而至于命,则性命之道毕矣。”
北宗对于性命的看法,和南宗基本上一致。如王重阳说:“性者神也,命者气也。”但因其贵性,故对性的议论甚丰。他们多以性来指人精神的先天本原或不变不动的本体,名之曰“真性”、“真心”、“元神”等。并谓这一真性不生不灭,本空本净,为超脱生死的可靠根据。王重阳说:“是这真性不乱,万缘不挂,不去不来,此是长生不死也。”丘长春说:“吾宗所以不言长生者,非不长生,超之也。”尽管南北二宗在一些看法与修持次序上有所不同,但皆以性命双修双了为第一要义。元李道纯融二宗之说,著《性命论》一篇,详论双修要旨。他说:“性者,先天至神,一灵之谓也。命者,先天至精,一气之谓也。性之造化系乎心,命之造化系乎身。见解智识出于心也,思虑念想心役性也;举动应酬出于身也,语默视听身累命也。命有身累则有生有死,性受心役则有往有来。是知身心两字,精神之舍也,精神乃性命之本也。性无命不立,命无性不存,其名虽二,其理一也。”这就把性命身心之说融和一处,佛道二家贯通一体。
他还批评了传统的“缁流道子”,谓其分性命为二,各执一边,互相是非,“殊不知孤阴寡阳皆不能成全大事。修命者不明其性,宁逃劫运?见性者不知其命,末后何归?仙师曰:炼金丹,不达性,此是修行第一病。只修真性不修丹,万劫英灵难入圣。诚哉言欤!高上之士性命兼达,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,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。身安泰则命基永固,心虚澄则性本圆明。性圆明则无来无去,命永固则无死无生,至于混成圆顿,直入无为,性命双全,形神俱妙也。”道教内丹家性命双修之旨,于此可谓披露无余。
明代丹经《性命圭旨·元集》有“尽性了命图”,并以日月的运转来说明性命双修的道理。书中说,丹田元精好比是日,心中元性好比是月,日光自返照月,“盖交会之后,宝体乃生金也。月受日气,故初三生一阳者,丹即居鼎,觉一点灵光,自心常照,而无昼夜,一阳生于月之八日,而二阳产矣。二阳者,丹之精气少旺,而元性又少现。自二阳生之于望,而三阳纯矣。三阳纯者,是所谓元性尽现而如月之圆也。月既圆矣,十六而一阴生。一阴者,性归于命之始也。自一阴生,至于月之二十三,而二阴产矣。二阴者,乃性归于命三之二也;自二阴生于月之三十日,而三阴全矣。三阴全,乃性尽归于命也。方其始也,以命而取性;性全矣,又以性而安命,此是性命双修大机括处。”
可见,性命二者乃同一本体的两方面的功能,所谓“本一,而用则二也”。这种从性命角度认识人体生命现象的方法,是道教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。
道教所独具的这种性命双修双了的养生学,和西方传统的养生学比较,有一个完全不同之处。那就是道教养生学不是单纯讲寿命、讲延年益寿的问题,而是整个人生修养方法。借这个方法,去完成人生的最高修养境界,即到达“天人合一”的大同世界。在西方养生家看来,健康长寿是养生学的唯一目的,故在他们的论著中仅仅局限于对体质与力量的论述,而不涉及心性与道德的修持。如被誉为西方养生学开山鼻祖和运动医学的创始人、古希腊的希波克拉第,著有《论养生》四卷,从养生法的原理到处方,论述得很全面。又著《论健康时的养生》,不仅阐述了饮食养生,而且从普通人到锻炼者如何确定运动处方都谈到了。这些著作的内容相当丰富,都是以饮食养生为中心而论述了涂油、按摩、洗澡、呕吐、绝食、睡眠以及运动等的处方,却没有一处谈及道德的修持。